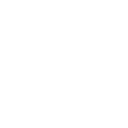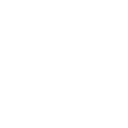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除了共和党历来比更支持平等权利和计划生育,《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女性健康都不是党派问题。“计划生育”是玛格丽特·桑格于1916年创立的避孕组织,但组织反对她的女权主义立场,因而在她1966年去世前几十年就强迫她退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一组织的领导人一直更倾向于共和党。到了50年代,这些人里很多都是保守派人士——巴里·戈德华特和他的妻子在“凤凰城计划生育委员会”(Planned Parenthood of Phoenix)任职——从政治上讲,计划生育已经成为一种家庭价值观。在推动避孕合法化的过程中,计划生育组织也得到了医生及神职人员的广泛支持。1958年,西奈山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产科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妇产科临床教授、计划生育医学顾问委员会成员艾伦·F. 古特马赫(Alan F. Guttmacher)向纽约市立医院提出质疑,要求撤销禁止医生发放避孕药具或提供避孕资料的医疗政策。医院的牧师们对他这一举动表示支持。1960年,计划生育组织神职人员国家咨询委员会(Planned Parenthood’s Clergymen’s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发布了一项名为“计划生育伦理”(The Ethics of Family Planning)的声明,称计划生育是在履行“上帝的旨意”,允许已婚夫妇仅仅为了爱而享受。
堕胎合法化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不是女权活动家,而是计划生育组织的医生、律师和神职人员。1962年,当古特马赫成为计划生育组织的主席时,他发起了一项运动,以确保联邦政府支持穷人的计划生育,解除避孕禁令,并放宽堕胎法的限制。1965年,前总统们——来自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和来自的杜鲁门一起担任了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联合主席,这标志着两党对允许避孕的共同承诺。那一年,在“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禁止避孕的州禁令,推翻了对康涅狄格州计划生育诊所负责人埃斯特尔·格里斯沃尔德(Estelle Griswold)的定罪(他因分发避孕药而被捕)。自玛格丽特·桑格因同样的罪名被捕以来,已过去了将近50年。但在“格里斯沃尔德案”中获得保护的避孕权并不牢靠。
但是,即便两党达成的广泛政治共识是支持计划生育的,但女性内部对其他问题的分歧也越来越大。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女性运动”实际上包括三种运动:激进女权主义、自由女权主义的和保守派反女权主义。激进派女性运动来自新,在那里几乎找不到对女性受压迫观点的任何支持。“让她们滚到一边去!”一名伯克利的学生领袖说。在被问到女性在黑人权力运动中的地位时,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回答说:“女性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极为卑下。”激进女权主义者为摆脱女性身份的约束以及柔弱特质的束缚而斗争。她们的论点一开始是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学,之后迅速转向了文化。1968年,纽约激进派女性苏拉米丝·费尔史东(Shulamith Firestone)为“传统女性”举行了一场葬礼,埋葬了一个金色鬈发的人体模型。1968年,在抗议“美国小姐”的选美比赛时,费尔史东的街头剧形式吸引了全国观众,激进派女权主义者给一只绵羊戴上了“美国小姐”的桂冠,她们在一个垃圾桶里焚烧束腰带、高跟鞋和《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并拉起“妇女解放”的横幅,大喊“为了女性的自由”!
虽然卡迈克尔那样说,但激进女权主义深受黑人权力运动的影响,这体现在它对自由主义的蔑视和对分离主义以及自尊主义的强调,并且与新生的同性恋权利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同性恋权利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变得强劲和激烈。1965年,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包围了联合国大厦、费城的独立大厅和白宫(包围白宫三次)。1968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同性恋权利会议上,参与者受到“黑即是美”这一标语的启发,称“同性恋即是善”。在1969年警察袭击纽约石墙旅馆(Stonewall Inn)的一年后,同性恋权利团体组织举行从格林威治村到中央公园的大。“我们必须公开站出来,不要感到羞耻,否则人们会继续把我们视为怪胎,”一名参与者说,“这次是对我们新的自尊心的肯定和宣示。”
相比之下,自由女权主义者从选举权运动、废奴运动和“黑人权力”前的民权运动中汲取灵感、借鉴经验。为了追求平等权利,她们想要通过法律、修正宪法、赢得诉讼案,并让女性当选,并进入政坛。1971年,作家格洛莉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共和党组织者塔尼娅·梅利奇(Tanya Melich)、纽约女议员贝拉·阿布朱格(Bella Abzug)和雪莉·奇泽姆(Shirley Chisholm)成立了跨党派的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National Women’s Political Caucus)。第二年,竞选公职的女性人数创造了纪录,其中就包括寻求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奇泽姆——她们不停地展开竞选活动。在1970年至1975年期间,当选公职的女性人数翻了一番。1971年至1972年的第92届国会通过了比其他任何一届国会更多的女性权利法案,其中包括《公共卫生服务法第九条》(Title Ⅸ)以及联邦《儿童保育法案》(被尼克松否决)。《平等权利修正案》在1923年首次进入国会,1971年以354∶24在众议院获得通过,1972年以84∶8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它在交由各州批准时取得了巨大胜利,以极大的优势获得批准,在自由主义的马萨诸塞州是205∶7,在保守的西弗吉尼亚州是31∶0,在无倾向的科罗拉多州是61∶0。
当法院快要对“罗诉韦德案”做出裁决时,尼克松的顾问们发现了一个政治机会。1971年,尼克松的演讲词撰稿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告诉总统,堕胎是“一个日益上升的问题,对天主教徒来说也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他建议说“如果总统公开表示反对堕胎,并将其视为对总统本人道德准则的冒犯”,他的连任前景将会得到改善。于是一周之后,尼克松抛弃了他先前对堕胎的支持,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提到了他“对人类生命神圣性的个人信仰——包括尚未出生的生命”。他利用天主教徒对堕胎的反对有意将教义绝对论带入政党政治。尼克松的支持者对此表示不满,问尼克松能否回到最初的立场上。布坎南把反对意见抛到了一边:“他若让自己失去天主教徒的支持,还能得到什么?贝蒂·弗里丹吗?”
与尼克松不同,贝蒂·福特没有在私下里表达过她对堕胎的真实看法。尼克松辞职几个小时后,她的丈夫就上任了,从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坦率地谈论妇女的权利、堕胎和妇女健康问题。她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自埃莉诺·罗斯福以来,没有任何一位会这样做。在她搬进白宫仅仅几周后,她就发现自己患有乳腺癌,需要进行紧急切除术。她决定不隐瞒这个消息,并鼓励女性接受检查从而挽救她们的生命——乳腺癌是当时25至45岁女性的头号杀手——她公布了她的病情,并允许人们拍摄自己在康复期间的状况。“我认为全国各地都有像我这样的妇女,”她说,“如果我不公开我的情况,她们就会失去生命或者处于危险之中。”她赢得了一大批极为忠诚的追随者,尤其是女性选民。
总统吉米·卡特于1976年当选,在他的执政期里出现的经济衰落和道德低迷被称为“萎靡不振”,大多数美国人是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禁运期间首次感受到低迷的存在。汽油的成本在几个月内增加了五倍,并推高了其他商品的价格。道琼斯指数在1974年的9个月里损失了37%的市值。生产更省油汽车的日本汽车厂商在与底特律厂商的竞争中胜出。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大多关闭厂房或搬到了其他国家,这导致在中西部出现了一条“锈带”(Rust Belt)。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这些奇怪而令人困惑的现象折磨着美国经济,经济学家们不得不为这些现象创造一个新的名字——滞胀(stagflation)。
一种符合部分证据(如果不是全部的线年的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经济增长是由发明驱动的,从电力到汽车都是不可持续的。1970年以后,发明的步伐放缓,成果有限。为美国的每个家庭提供电力、燃气、电话、用水、疏通下水道,也就是取暖、通信和清洁等方面的工作,大约在1940年已经完成,使人们不再互相隔离,并在生活条件和经济产出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1970年以前的医学进步,包括麻醉、公共供水系统、无菌手术、抗生素和X射线,挽救并延长了人的生命。但在1970年以后,很少有发明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相反,它们所提供的改善是缓慢而平稳的。手机很有用,但电线年突破了声速,再快则不切实际。此外,1970年以后,不断出现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成了美国的生活特色,这意味着新发明的经济利益不成比例地为极少一部分人所享有。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即便更多的女性外出工作,家庭收入也并没有因此而增加。自由主义者指责保守派,保守派指责自由主义者,而施拉夫利则说服了很多人指责女权主义者。她在1972年写道:“女性自由主义是对美国妇女角色的全面攻击——作为妻子、母亲,以及在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施拉夫利最初并没有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但是她后来解释说,她逐渐相信这是一项针对女性法定特权和应有保护的阴谋。她把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与联系在一起。她说,苏联女性就拥有“平等的权利”,这意味着母亲被迫“将孩子送到国营托儿所或幼儿园,这样她就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早些时候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乔治·华莱士那一年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参选时,改变了立场,他的竞选纲领是:“美国党的妇女要对这个阴险的社会主义计划说‘不’,这一计划会摧毁家庭,让妇女成为政府的奴隶,让她们的孩子成为国家的被监护人”。
在1972年的共和党大会上,共和党女性为恢复该党赞同《平等权利修正案》的纲领而奋斗。为了包抄她们,施拉夫利小心翼翼地集结她的队伍,并贮备意识形态方面的武器,组建了一个名为“STOP ERA”的妇女组织,和对立派的STOP相同,但它是不同名词的缩写——“不能剥夺我们的特权”(Stop Taking Our Privileges,STOP);ERA指《平等权利修正案》),她将部队一路开进前线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一群共和党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共和党妇女特别工作组(Republican Women’s Task Force),为使《平等权利修正案》、生育权、平权措施、联邦政府出资建设的幼儿园以及扩充《同酬法案》(Equal Pay Act)进入党纲而斗争。她们还支持赞成《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杰拉尔德·福特作为党内总统候选人,而不是罗纳德·里根。她们只获得了一场惨淡的胜利。福特赢得了提名,但是,党纲小组委员会以一票之差否决了《平等权利修正案》。只是由于福特的激烈游说,《平等权利修正案》才以51∶47在党纲总务委员会惊险过关。
全国妇女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自由派女权主义的高潮,这是第二次制宪会议。自1848年在塞尼卡福尔斯召开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以来,已经过去了漫长而艰辛的125年,那次会议为期2天,当时有300人参加。在1977年的休斯敦,来自50个州的2000名代表以及2万名与会者进行了为期4天的会晤,制订了一项26点的“国家行动计划”。1500名记者对会议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这主要是因为会议聚集了全美的女性名人,包括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网球冠军比利·简·金(Billie Jean King)、“罗诉韦德案”的律师萨拉·韦丁顿和来自电视剧《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的琼·斯特普尔顿(Jean Stapleton),她在其中饰演艾迪斯·本克(Edith Bunker)一角,从中她感受到蓝领家庭主妇的无言痛苦。
大会提出的两项最具争议的建议是呼吁政府为堕胎提供资金,以及承认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享有平等权利。弗里丹对同性恋权利运动尤其深恶痛绝,她认为这会破坏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她公开表示对女权主义与女同性恋之间的任何联系感到遗憾。那一年早些时候,流行歌手兼四个孩子的母亲阿妮塔·布莱恩特(Anita Bryant)发起了一场被她称为“救救我们的孩子”的运动。她希望能让孩子们免受男女同性恋教师的影响(她暗示,这些老师会把同性恋思想灌输给孩子们,还会孩子们)。曾经是俄克拉何马州小姐的布莱恩特现在住在佛罗里达州,是南方浸信会成员,她反对迈阿密禁止就业中性取向歧视的法令,警告人们所多玛和蛾摩拉的覆灭。布莱恩特的努力适得其反。当妇女大会在休斯敦开幕时,布莱恩特对她所谓的“一个组织良好、资金充足、政治激进的同性恋活动家群体”的讨伐已经使得许多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开始支持同性恋的权利,即便她们以前并不愿意支持。
除了几个例外,一个多世纪以来,福音派一直与政党政治保持距离。自从反蓄奴运动之后,新教教会也从不进行明显的政治活动,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福音派人士加入了保守派革命,决心要保护家庭和教会不受国家影响。最高法院做出的一系列裁定促成了这一转变。1961年,法院推翻了马里兰州要求雇员表明信仰上帝的法律。1962年,它宣布学校强制性祷告属于违宪,并且在1963年的两项裁定中废除了学校里其他形式的强制性宗教表达:阅读《圣经》和背诵主祷文。接着在1971年的“科伊特诉格林案”中,法院裁定,实行种族隔离的私立学校没有资格获得免税的待遇。“科伊特诉格林案”之后,私立宗教学校无法再为反对融合的白人提供避难所。受到美国国税局调查的南方教会学校,包括鲍勃·琼斯大学和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是由南方浸信会教徒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管理的。福尔韦尔一直是《往日福音时间》(Old-Time Gospel Hour)民间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这档节目每周一次,带有二三十年代的风格。福尔韦尔也凭借这档节目获得全国各地的追随者。福尔韦尔黑色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坐在幕布前,双手放在《圣经》上,用浅显而朴素的语言布道。“科伊特诉格林案”是一个没有伴随解释的裁定,除了所涉及的学校,该案在一开始很少受到外界的关注。后来,对那些拥护种族隔离的冷战保守派分子来说,它有了用武之地:作为一系列裁决中最新的一次,他们攻击它既没有体现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承诺,也没有遵循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局案”中的判决,而是助长了的势力。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说:“这种将上帝从我们的国家生活中根除的动力就是认识到美国在世俗化之前是无法有效地进行社会化改革。”
传统基金会的创始人保罗·韦里奇和前戈德华和党人兼广告直邮经理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guerie),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通过在各种问题上吸引福音派人士的注意,从而将他们引入新的保守派联盟。他们很快就招揽了福尔韦尔,后者在1979年创立了“道德的大多数”(Moral Majority)——这个词是韦里奇模仿尼克松的“沉默的大多数”创造的——以反对“世俗人道主义”。福尔韦尔丢掉了他平实的布道风格,变得越来越尖锐,他宣布:“我们正在打一场圣战,而这次我们将赢得胜利。”为了发动这场圣战,福尔韦尔针对一些问题召集他的追随者,而施拉夫利已经围绕着这些问题招募了一支军队:反对同性恋权利、性自由、妇女解放、《平等权利修正案》、托儿所和性教育,以及最重要的——反对堕胎。
福尔韦尔后来强调,对他而言,这一政治运动在1973年得知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裁定时就已经开始了。但事实远非如此。事实上,南方浸信会在此之前就曾为堕胎法的自由化而斗争。1971年,在密苏里州召开的浸信会教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我们呼吁南方浸礼会教友为立法工作,使在、、有明确证据表明胎儿严重畸形以及经仔细检查确认会损害母亲情绪及身心健康等情形下的堕胎成为可能。”南方浸信会大会在1974年重申了这一决议,并在1976年使用了类似的表达方式。另一位南方浸信会牧师、基督教广播网(the 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的创始人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称堕胎是“一个严格的神学问题”。福尔韦尔想法的改变和从福音派转而反对堕胎使一些天主教徒感到他的落伍和虚伪。1982年,美国生命联盟(the American Life League)的创始人不无讽刺地说:“福尔韦尔五年都不会写‘堕胎’这个词。”
对共和党来说,审判的日子已经到了。自1966年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以来,69岁的里根一直是该党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人士,尽管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右翼的立场。虽然他在197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输给了温和的杰拉尔德·福特,但里根及其忠诚的支持者似乎认为,他领导国家的时间现在终于到来了。里根得到了施拉夫利的支持,而且福音派人士此时也加入了保守派联盟。在竞选期间,福尔韦尔据说走了大约30万英里,“道德的大多数”组织声称在47个州都有分会,并已登记了400万选民。帕特·罗伯逊和来自校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的比尔·布赖特(Bill Bright,又译白立德)一起在华盛顿筹划了一个有25万保守派基督徒参加的耶稣集会。他们接管了南方浸信会,并在1980年通过了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堕胎和同性恋的新决议。党内的温和派——特别是女性——进行了反击,希望留住权力。在该党1980年年底特律大会的第一天,威廉·洛克肖斯的妻子,有时被称为“共和党的葛罗莉亚·斯泰纳姆”的吉尔·洛克肖斯(Jill Ruckelshaus)在12,000人的平等权利集会上发表讲话。她穿着女性参政主义者的白色服装。“我们党已经拥护了《平等权利修正案》40年,”洛克肖斯指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理查德·尼克松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杰拉尔德·福特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然后她恳求道:“把我的党还给我!”
“因为保守派掌握了新技术,”维格里写道,“我们已经能够绕过对国家新闻媒体近乎垄断的局面。”维格里认为,新并没有真正的新想法,它有的是新工具:“使用计算机、直邮、电话营销、电视(包括有线电视)、收音机、录音带和免费电话以及其他方式要求捐款和投票。”维格里是直邮竞选活动方面的专家,他用人口普查、活动财务记录、民意调查和选举数据来定位单个家庭。维格里在1980年报告说:“保守派已经确定了大约400万名捐助者。”16年之前,他制作了第一份名单,上面记录着向巴里·戈德华特捐赠50美元及更多款项的12,000名美国人的姓名和地址。“我估计自由派已经确定捐赠的人不到150万。”直邮和有线电视将选民分割开来,也将公众分成小块群体。保守派没有浪费精力与他们希望接触的目标人群之外的选民交流,这为他们节省了资金,提高了竞选效率;新技术还为候选人进行抨击提供了动机。最重要的是,它允许保守派绕过大众媒体、报纸和广播电视的守门人——他们越来越像保守派眼中的敌人。
在新的崛起中,几乎发挥同样影响力的是民意调查行业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乔治·盖洛普的儿子小乔治,一个虔诚的圣公会教徒,开始利用民意调查来评估福音派运动的力量,尽管如评论家指出的那样,民意调查中经常去教堂的美国人所占比例过大,他们的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使他们比他们的同胞更有可能参与调查。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要给予民意调查更广泛的关注”再次出现在70年代。1972年,政治学家利奥·博加特(Leo Bogart)证明了大多数民意调查所做的事情是制造舆论,因为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所调查的主题和事项几乎一无所知,也几乎没有任何意见。“民意调查员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博加特写道,“‘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意见吗?’”随后,国会对该行业的调查再次带来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问题,包括关于民意调查的准确性,以及它们在民主制度中的地位,但拟议中的“民意调查真相法案”未能获得通过。相反,随着配备了电脑的新闻媒体开始展开自己的民意调查,民意调查得到了发展和扩张。在1973年出版的《精确新闻报道:记者应掌握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Precision Journalism:A Reporte’s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 Methods)一书中,俄亥俄州阿克伦市一家报纸的驻华盛顿记者菲利普·迈耶(Philip Meyer)号召记者们进行自己的民意调查:“如果你的报纸有一个数据处理部门,那它就有键控穿孔机和操作人员。”两年后,《》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了一项联合民意调查——这是首次媒体调查。批评人士指出,从道德角度来看,应该报道新闻的媒体不能同时制作新闻,但媒体发起的民意调查仍然如火如荼。
和内战前几十年的情况一样,当福音派再次进入政界时,党派政治就呈现出宗教的狂热。惊慌不安的政治科学家设计了新的方法,用来量化美国人日益增长的政治热情,包括通过分析唱名投票来衡量国会议员中的两极分化。从衡量结果看,国会的两极分化在内战结束后不久开始下降,并且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随着共和党变得更加温和而持续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当共和党人变得更为保守时,两极分化开始尖锐起来。南方人向共和党的转移只占这种转变的三分之一。这种转变更多的是堕胎政治化的结果。从1978年到1984年,支持生命权的人和支持选择权的共和党人被赶出了各自的政党。在里根之后,似乎出现了所谓的性别差。从妇女获得选举权的1920年至1980年间,女性倾向于不成比例地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投票——如果说差距还很小的线年发生了变化,当时有更多的女性投票支持卡特而不是里根,两者差距为8个百分点,可能是因为已开始将自己定为女性党造成的。共和党战略家的结论是,在(白人)女性与(白人)男性的交换中,他们得到了更好的结果。一位共和党顾问在提到时说,“他们在男人中表现得非常糟糕,以致我们在女性中表现不佳的事实,变得无关紧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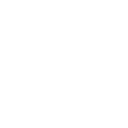

@HASHKFK